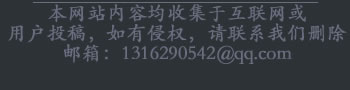首页 > 最新信息 / 正文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六章传教士对汉学的思想史研究
引言
在那套著名的《海外传教士耶稣会士通信录》一书中,记录了巴波提斯特教士(Jean Baptis te Lou)研究汉学的情况时说:“他用三十多年的时间刻苦研读古代经典著作。”《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par Quelques Mis 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 Orientales》,由日文本《エイズス会士中国书简集》译出。平凡社,昭和45年。这并非是巴波提斯特 教士本人才有的特殊现象。特别是1574年在澳门举行的对华传教工作会议之后,在华传教士 们都曾有过下苦功夫去学习汉语的过程。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传教士来说,至少要用十年时 间学习汉语才可以进行汉学研究。在上述一书中,有的传教士在致西方教友的书信中声称: 只用二年多就认识了所有的汉字。这类书信并不可信,其目的除了自吹可能就是为了打消正 在准备来华传教的西方人学习汉字的畏惧心理吧。
这个十年的时间期限是由当时俄罗斯帝国东正教比丘林教士在1816年11月根据以往的实际经验提出来的。他把十年的时间分为三段:第一段计五年时间:进行汉语为主、以满·蒙·藏 语为辅的语言学习阶段。第二段计三年时间:进行儒家经学为主、以史学·佛学为辅的专业 知识学习阶段。第三段计两年时间:进行对古代中国某一专题的特殊研究阶段。
这十年的期间和三阶段的学习、研究过程,和今日外国大学中的从本科开始到取得博士学位 为止的培养汉学专业研究人员的路数大致是一致的。俄罗斯帝国东正教的比丘林教士成了现 代国际社会汉学教育体系的当然奠基人。同时也为俄罗斯帝国时代汉学研究的基本倾向奠定 了基础。整个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汉学发展的历史,正是由对汉、满、蒙、藏语的研究以
及在利用上述史料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为核心的。
当然,有成就的汉学家,特别是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汉学家,至少要在通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去 研读一遍中国古代的最基本的经、史著作,才有可能对自己感兴致的研究课题作出有创见又 成体系的论述。在本章中所论述的汉学家们,每个人都有二、三十年左右的研究汉学的经历 。他们对汉学在西方学术界的传播,其贡献之巨大是世人皆知的。
第一节语言文字学研究
要想研究汉学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必须通晓汉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读书须先识字”是一个 最为基础的前题。当然,在这里,“识字”是指对文字训诂学的研究。
其中,汉字和汉语语法又是通晓汉语的关键。的确有一些汉学家在既不会说汉语又不了解汉 字的情况下,正在进行着汉学研究。这在日本,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945年以后日本国政府规定的当用汉字和常用汉字的总数,大约和一个普通的中国小学生所认识的汉字数量相当。因此在读中文著作时,在对文义的理解上一般不会出现太大的误解。至少可以接受三分之一左右的正确的内容。对于不会日语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两国共同使用的汉字都会出现在中、日文的汉学研究著作中,使得一些不了解对方语言的人也可以进行汉学或和学的“研究”了。对西方人来说,在不会说汉语的情况下进行汉学研究,就更为艰难和困顿了。不亚如破译已经无人使用的远古时代未知部落的古文字。因此,西方传教士们所面对的第一个任务就学习汉语。传教士在学习汉语过程中留下的研究汉语和汉字的著作,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可资立论的证据。
第一、金尼阁和《西儒耳目资》
传教士们在国内使用的是欧罗巴语系的字母文字,到了中国以后才开始学习作为象形文字的 汉字。这其中的诸多文化和思想上的区别也在对汉语和汉字的学习过程中体现出来。如,16 26年出版的由金尼阁教士所作的《西儒耳目资》一书。这是第一部以西方近代语言学理论来处理汉语和汉字的一部工具书。如,对汉字的注音方法是以“音标符号总数不过三十上下,展转拼合,再调以中国五声,便可把明末普通音,赅括无遗”,这一方法使汉语和汉字的表达方式产生了一种革新,即:首先在读音上把汉字和欧罗巴语系统一起来。利用欧罗巴语系中的对字母的注音方式——也即对语素的分析,以此作为对汉语和汉字的分析、处理标准。传统的反切式注音和分析方法被彻底革新。这部字典式的工具书的出现,为传教士们对汉语和汉字的研究拉开了序曲。在这里的“再调以中国五声”是指在《西儒耳目资》一书中,金尼阁教士把汉字分为清、去、上、入、濯五个声调。就这一区分方法,《利玛窦中国札记》 一书曾评价说:“采用五种符号来区别所有的声韵,使学者可以决定特别的声韵而赋予它们 各种意义”。这为传教士们的汉语学习提供了方便,也使传统的中国音韵学走向近代学术体 系中。
第二、传教士的汉字研究
1628年,赫尼斯教士(Justus Heurnius)曾编纂一部中·荷·拉丁文三用的大辞典。1641年,鲁德照教士曾著有《汉葡字书》和《葡汉字书》各一部。相传,葡萄牙的费奇规教士也曾著有《汉葡字书》一部。以上几部辞典,可惜均未出版。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字典可能是1685年,由门泽尔博士所编纂的《字汇》一书,这是以拉丁文来解释中文的一部字典。门泽尔博士本人是一个医生,他利用柏应理教士短期回国的机会,就师从柏应理教士,开始了汉语的学习。除此之外,这位医学博士还有一部未出版的汉语辞典《中文语汇》(《Lexicon Sinic um》)。
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有关地理、历史、年代和政治的记录》一书的第二卷中,就专门收有传教士研究古代汉语语法问题的论文。除此之外,还有不少手稿本著作迄今尚未出版。如,作于1752年的《中法辞典》(《Dictionnaire Francois Chinois》),作于1740年的《中·蒙·佛文辞典》(《Dictionarium Sinico Mongolico Gallicum》)等著作。1813年,格蒙纳教士(Basilio de Gemona)所作的《中·拉丁文辞典》(《Dictionarium Sinico La tinum》)一书出版。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
当时某传教士在一封信中,很有代表性的表明了西方国家的传教士们对汉字的看法:“某一 个汉字是单纯的文字,而其构成则由两个或多个近似字母的偏旁和部首组成的。一般来说, 汉字是由象形的,或由象形文字的某一要素组成的。并以此作为汉字的核心。在表达意义上 的大字母式的象形文字和表达发音的一些小字母式的象形文字的组合,构成了一个汉字的读 音和意义。”《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 ge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de la Chine et des Ind es Orientales》,由日文本《エイズス会士中国书简集》译出。平凡社,昭和45年。早期传教士们的对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带有十分明显的欧罗巴语系语法理论色彩,总想通过汉字的六书构成汉字的规律,找出几点和欧罗巴语系字母文字相一致的构成汉字的字母意义上的规律。这种研究和学习,并不是中国古代的训诂学意义上的内容、也不同于古代汉语音韵学意义上的内容。在这种带有欧罗巴语系色彩的汉语和汉字研究著作中,对语素的分析和注音,是把传统的训诂学和音韵学的研究引到现代社会的先锋。这是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不过当时的西方,因为埃及学、巴比伦学的不发达,致使还没有出现东西方象形文字的比 较性研究的著作。
第三、汉语语法学的研究
欧罗巴语系的语言,在语法上和汉语的最大差别是:对动词的时态性使用和与之相一致的动 词的规律性变格现象。这一差别也是由文字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即由象形文字和字母文字 的不同所决定的。
在汉语语法体系的研究上,马若瑟教士(Joseph Heinrich de Premare)所作的《中文语法研究手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一书,是早期西方汉学史上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结构的一部力作。此书的手抄本一直是西方汉学家学习汉语的必备著作。如,十九世纪法国大汉学家儒莲(Stanialas Julien)等人就曾使用此书作为教材。
当时,初学汉语的某传教士在一封信中说:“我当时想像:汉语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一种语 言,但是到了熟悉汉语以后,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没有比汉语的表现力更贫乏了。中国人要 掌握六万多个汉字,他们不能用汉语准确地表达出用欧洲语言所能表现出的所有的事情,为 了把自己的意思向对方表达清楚,他们不得不借助很多的汉字……汉字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变 化,这些汉字并不是表达同样的事情,汉字的读音又没有太大的变化。当说出某一单词时, 常常语意不明,听者把说出的读音记录成文字的话,如果没有在眼前放着所说的那种东西的 话,就很难理解所说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在欧洲,人们一般认为汉字数量之多是汉语丰富 的一个证据,但如果稍知一点实情并能对此加以考虑的话,这显然是词汇贫乏的一个印证了。汉语的文字由六万多个汉字构成,如果拉丁语的所有词汇都以单个的字来表达的话,那么拉丁语在使用单字的数量之多是无法比拟的。和拉丁语相比,在词汇的数量上远远不如的是法语。但是和汉语相比,还是优先的。因此上,欧洲的二十四种文字可以把各种母国语言使用者的意图表达出来,而在中国,以惊人数量的汉字和不能准确判定到底为何字的读音来进行交流,大概不能马上把真正的意义传达给别人吧。”《Lettres Edifiantes et C 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 nie de Jesu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 Orientales》,由日文本《エイズス会士中国书简集》译出。平凡社,昭和45年。从这封来信中,我们可以发现:欧洲语言学界中的那种单字数量多必然词汇的组合变化就少的近代欧罗巴语系的语言学基本观念和特征正主导着传教士们的古代汉语研究,并成为他们进行古代汉语研究的理论基础。不过,所谓“以惊人数量的汉字和不能准确判定到底为何字的读音来进行交流,大概不能马上把真正的意义传达给别人吧”的话,和文中所说的“熟习汉语以后”是矛盾的。这说明此信作者的汉语水准还远远没有达到“熟习汉语”这一程度。此信的产生只能是在进行汉语学习的入门阶段的体会。
其实,比较语言学理论成立的基础并不是以拉丁语或法语为前提的。汉语的表现力在上古汉 语中的确是以不同的汉字来进行的,这就客观上促进了汉字数量的增多。因为复合词汇的大 量产生是中古汉语时代中的事情,在上古汉语时代里复合词汇并不多,进而组合变化也就少。但这是语言在使用年代久远的一种共同标志。而汉语的先进之处正是能以多重汉字的产生 来表达准确的意图,在原始时代,甚至到了上古时代,如果不增加文字,就只能增加使用中 的误解。这对汉语和象形字的汉字来说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和欧洲语言中的那种以字母的多 重组合和单字在介词参与下的不同组合是完全不能进行优劣比较的两套并行语言系统。
第四、其他
1684年,黑德教士(Thomas Hyde)出版了他编纂的《标准北京话》(《Specimen Lexici Mand arinici》)一书,此书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研究明清之际北京话的发音和方言用语的工具书性的教科书。门泽尔博士编纂的《初级中文》(《Clavis Sinica》)一书,是十七世纪晚期一部没有出版的有关古代汉语语法和日常会话用语的入门性著作。
马若瑟教士的《中文语法研究手记》一书,是当时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一部名著。此书使用 了五万多个汉字,并附有一万二千多条当时汉语的用语实例。但是因为使用汉字太多太难, 当时的法国和欧洲各国因无法解决印刷制版问题,致使此书一直没得到正式印行。不幸的是,此书的手稿本被他的学生艾提恩耐(Fourmont Etienne)借走后加以剽窃,并以《中文文法》(《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hicae Grammatica Duplex》)作为书名,1742年正式出版,开创了东西方汉学史上一个恶的先例。至于马若瑟教士的《中文语法研究手记》一书直到1831年才得以正式印刷出版。尽管如此,马若瑟教士的《中文语法研究手记》一书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对始自宋元时代正在兴起的汉语口语(白话)和始自汉唐时代的标准书面语(文言)进行了区分。
1815年,由莫瑞逊教士所编著的《中英辞典》(《A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第一册第一卷正式出版。1822年,该书的第一册第二卷出版。1823年,该书的第一册第三卷出版。1819年,该书的第二册第一卷出版。1820年,该书的第二册第二卷出版。1822年,该书的一卷本的第三册出版。以上共由三册六卷构成。其中,仅在第二册是以明代的《五车韵府》和清代的《康熙字典》为基础而作成的。此书出版后,立刻成为西方汉学界以西方文字解释汉字最为权威的一部工具书。当时的法兰西学院的第二任汉学教授儒莲曾评价说“这是以欧洲文字来解释汉字的最为优秀的著作”。
1835年,比丘林教士出版了由他本人编写的《中国语文法》一书。
第二节中国古代史研究
传教士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依研究内容和专题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 专题研究三种。我在此分析一下他们进行这一研究的思想史意义。
第一、通史研究
1584年,门斗撒教士所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是西方汉学史上第一部有关中国古代史 的通论性专著。此书是以当时通用的西班牙文写成的。此书在介绍中国文字时,又第一次把 汉字印刷出来。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法、英、德等国文字。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此书居然介 绍了中国古代佛教、道教的一部分历史和有关知识。或许,在此意义上开启了以后西方汉学 界研究中国宗教的先河吧。
戴密微博士(Paul Demievlle)在《法国汉学研究的历史回顾》(《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学研究の历史的展望》)一文中评述说:“书中把中国美化了一番,没有贫困,没有乞丐。‘聪慧而又贤明的’人民,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遥远的国度呈现在他们面前。见1966年3月15日Paul Demievlle在日本京都大学所作报告。原文为法文,名 为《Apercu Historique des Sinologques en France》。日文由兴膳宏、川胜义雄、大桥 保夫共译,名为《フランスにおけるシナ学研究の历史的展望》,刊在《东方学》第33 、34期。中文由胡书经译,刊在阎纯德主编《国际汉学》第一集。但中文乃利用《东方学》 上所刊日文译出。当然,戴密微博士是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门斗撒教士的这种中国 观的。
在史料的使用方面,门斗撒教士的此书直接利用了佩瑞若的《中国报道》和克鲁兹的《中国旅行新志》二书。这又开启了利用史料进行书斋型汉学研究的先河。1605年,利玛窦教士出版了《古代中国》(《Musaeum Sinie》)一书。1641年,鲁德照教士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著作《中华大帝国史》一书,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1678 年,米勒教士的《中国历史》一书正式出版。
以上几部在西方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的中国历史研究和介绍著作的出版,对于改变当时以旅行 记为主的风俗性和知识性、猎奇性的介绍中国和中国史的局面有重大地促进作用。
1725年,赫尔德教士(Jean Baptiste du Halde)编著的多卷本著作《中华帝国全志:有关地理、历史、年代和政治的记录》(《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 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Iɾmpire de la Chine et de Tartarie Chinoise》)一书正式出版。方豪博士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评价赫尔德教士编著的这四大册的巨著说:“此书行世后,欧洲学术界、政治界与宗教界人士,对中国乃获得有系统的认识,虽不完全,若干方面,亦不甚正确,但较之以往,确已大有进步。而欧洲之汉学,乃由此而奠 定基础;法国早期之能执汉学界牛耳,此书亦不为无功。”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
1776年,钱德明教士的《中国古今音乐史论》(《Me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 nt Anciens que Modernes》)一书正式出版。从1777年开始,冯秉正教士所留下的多卷本遗著《中国通史》一书正式出版。1785年,格瑞斯尔(Grasier)出版了《中国史》(《Descri ption generale de la Chine》)一书。
从门斗撒教士《中华大帝国史》一书,到冯秉正教士的《中国通史》一书出版为止,中间经 过了近二百年,产生了各种西文的中国通史性著作不少于二十部,才有了一套比较满意的多 卷本、系统地研究和介绍中国古代通史的著作!
早期的传教士们进行有关中国通史研究的两个重要特点是:其一,希望能从中找出一条和《圣经》的创世时间记录相一致的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以此达到汉学研究和传教的一体 化。这和早期传教士们的通过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来证明基督教教义的普遍性是一致的。其二,在对中国古代通史发展过程的叙述上,以对军事·战争史、人物政治·事件史为核心。在这一点上和当时西方传统的史学理论和史学著作叙述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对上古历史和经书的研究是出自同一个目的。因此,从史学角度来看,早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有着更多地介绍性色彩,如,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一书以及和它同名的著作,这时的传教士汉学家们还没有脱离欧洲的传统史学理论去解说古代中国的历史。
在对古代中国历史进行介绍上,集大成著作是:《中华帝国全志:有关地理、历史、年代和 政治的记录》和《中国通史》二书。此二书在阐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时并没有以耶督教的 创世说为中心,尽管他们都在书中体现了古代中国的远古时代和《圣经》创世说的若干相合 之处,但对中华帝国的总体发展的说明和介绍以一种游记性、猎奇性地叙述来进行,在没有 任何史观的影响下(《圣经》创世说在此不能算作一种史观吧)完成了对中国古代通史的说明 ——这一工作的意义是重大的!
第二、儒家历史观的研究
钱德明教士的《中国古今音乐史论》一书在1776年出版后,对中国通史的研究开始和欧洲传 统的史学理论结合起来,走出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督教神学色彩。于是,对中国历史的介 绍变成了对中国历史的阐释。而这一阐释又以儒学和史学的结合,即:以古代儒家思想中的 五行学说、政治道德学说为基础,去研究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
诚如福赫伯博士在《德国各大学的汉学研究》中所说:“十七、十八世纪的汉学着重于儒家 经典及儒家历史观的研究。故在此等作品中完全出于对民族传统的自负与中国文化理想化的 写照。西方人仍然不了解中国的宗教如道教、佛教,甚至于各种不同的文学类型,像抒情诗 和白话散文,更别提一些特殊情形了。欧洲人只接受真正合乎理性主义与启蒙主义思想的那 一部中国文化。十九世纪的汉学,一般而言仍保持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潮流,是一种浪漫式 的汉学,含有帝国主义,实证主义,及历史主义的思想。同时,汉学也因此而客观化,并且 逐渐提高地位成为一门主要的学科。”Gauting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 eutschen Universitaeten, Wiesbaden》,译文引自《东方杂志》复刊第20卷第八期。这里所说的“历史主义的思想”,即是反映了传教士们希望在对儒家历史观的研究中能印证出欧洲传统史学思想中的那种对历史发展进行规律性说教的内容。在我看来:对汉学进行的任何一种方式的研究,一旦进入到史学规律的阐释,也就完全脱离了起初的宗教性的意义追求,变成一种文化理性主义的附庸。直到今天,比如著名的“剑桥版”的系列中国通史的著述,都可以发现西方汉学家们在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时所追求的那种文化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子。
但是反对这一变化的历史学家,如,奥威尔斯博士(Pascal Oeuvres)认为:
Which is the more credible of the two, Moses or China?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s eeing this summarily. I tell you there is in it something to blind, and somethin g to enlighten, By this one word I destroy all your reasoning. “But China Obscu res”, say you:and I answer, “Chin a obscure but there is clearness to be foun d seek it.”引见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4 0年。
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中评述奥威尔斯博士的观点说:“这位中国史的反对论者,甚至以墨西哥的历史传说,来比拟中国古史,认为一样无稽,实际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旧教的拥护者……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 馆,1940年。
卫三畏教士在1848年出版的《中华帝国》一书,是美国汉学史上早期年代里研究古代中国史的代表著作。
案。
1684年,“外国传道会”(“Societe des Missions Etrangeres”)来到中国。进行有关礼仪问题的正式考查,并对耶稣会传教士的宽容派作法不满。
第一、仰慕圣化的汉学
“礼仪之争”的结果,当然是以传教士研究汉学并在传教时以对中国的部分顺从为主。如, 康熙帝南巡杭州时,殷铎泽教士亲自出来迎接,并行跪礼。康熙帝见之大喜。此事被记录在 《熙朝定案》等史册中,明显看出基督教和西藏喇嘛教的本质不同。又见礼部尚书顾八代代 表康熙皇帝公布的指令中有云“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渡海而来”者,可见在当时清 政府眼中,传教是出于“仰慕圣化”,并非如东土大唐前来取经之旧事。
“仰慕圣化”的重要表现是学习儒家思想,即研究汉学,而不是来华传教。康熙下令命传教 士学习经典,其目的有反传教、变被动为主动的因素在内。在方豪博士《中国天主教史人物 传》一书中公布的梵帝冈图书馆中所保存的白晋教士和傅圣泽教士二人奉康熙皇帝之命开始 学习《易经》的文献中,其中第三件特别说明了康熙对传教士研究中国思想目的之担心:“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出己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不可因其不同道即不看”。即,康熙皇帝最担心的是传教士不接受汉学思想。他两次告诫“不可因其不同道即不看”汉学著作。这最后一句话才是康熙的一针见血之处:“因其不同道即不看”这是传教士对待中国思想的最真实的态度。而对传教士来说,他们是来传教的,不是来取经的。研究汉学与否不能和传教事业相脱离。而当时传教士的答复有明显地敷衍成分:“凡中国文章,理微深奥,难以洞彻;况《易经》亦系中国书内更为深奥者”。这话出自一个已精通汉语的传教士之口,其对汉学思想的接受程度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白晋教士和傅圣泽教士又请出了在华耶稣会士会长的指令来对抗康熙皇帝的儒学宣传:“尔等所谓御览书内,凡有关天教处,未进呈之,当请旨求皇上谕允其先察详悉。……然不得不遵会长命”。因此,在第五件中,说明了传教士研究易学的目的是印证中国思想“与天教大有相同”、“无不合于天教”。即:这种态度使康熙皇帝和其大臣们的那种传教是出于对中国“仰慕圣化”而来观念落空了。因此,最后康熙皇帝无奈地说“作亦可,不作亦可”。
不过当时,在华传教士们对中国古代思想和儒家礼仪有其特殊的理解。见康熙三十九年十月 二十日闵明我教士(Philippus Maria Grimaldi)等人上康熙皇帝的奏文:“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以儒礼亦无求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还如在之意耳。至于郊天之礼典,非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尤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以上的理解,实际上就已把中西礼仪之争的诸多实质性问题化解开了。换句话说,这封奏文要说明的是:中国思想和儒家礼仪只具有伦理上的意义,而不具有宗教上的意义。这是当时一部分传教士的理解。
第二、七点禁令
1693年3月26日,罗马教皇派特使到福建省,又下达了中国信徒不能参加祭孔祭祖仪式、但承认在中国有此现象存在的命令。这只是前奏。
1704年11月20日,罗马教皇格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us XI)又正式发布了七点禁止令。此禁止令的名称是《自此开始》(《Ex Illa Die》)。全文如下:“一、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语。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只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取下来,不许悬挂。二、春秋二季祭孔,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教相同。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或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子庙行礼。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再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

本文作者:IAHLS通讯(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687126725140152835/
声明:本次转载非商业用途,每篇文章都注明有明确的作者和来源;仅用于个人学习、研究,如有需要请联系页底邮箱
- 搜索
-
- 05-31为什么说曹操对于汉献帝也是“仁至义尽”?
- 05-31他在郭嘉后二次定辽东,献计曹叡以少胜多吓退孙权(4)
- 05-31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 05-31“吃货”溥仪,5岁时每天吃27斤大肉,8只鸡鸭,背后有何隐情
- 05-31李煜:我在这人世流浪,梦一场痴心妄想
- 05-31清代户部官员为什么收入高
- 05-31卫子夫为何深受武帝喜爱?一介歌姬是怎么登上后位的?
- 05-31四十年代初的山西,抗战游击区朔州
- 05-31郭嘉不死,卧龙不出,郭嘉跟诸葛亮是一个级别的谋士吗?
- 05-31从清澈到浑浊:明代言官的兴衰浮沉
- 1000℃王宝强再谈离婚:别把老实人逼琴倾天下到极限
- 1000℃方华_方华最新消息,新闻,图片,封闭针的副作用视频_聚合阅读
- 1000℃妻居一品nppsy专访范扬:有着体育精神的国画大师|范扬|体育|国画
- 1000℃迎接世家传方略界环境日公交车变身“环保车箱”|公交车|环保|志愿者
- 1000℃毒贩为何能冲出博罗实验学校潘梦莹法庭跳窗逃跑?法院:查清后会问责|开发区|法院|毒贩
- 1000℃国奥巴马抓大盗中文版家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江苏用最严格制度保护海洋|督察|海洋|海洋生态
- 1000℃“赶一点太空帝国4秘籍进度就能早点缓解交通压力” 南京地铁7号线工地国庆“不打烊”|工地|打烊|早点
- 999℃江苏海安:召开审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山竹 县纪委大大上廉政党课
- 999℃英语单词揭鉴黄警察:持证上岗 半年鉴定5万部淫秽视频|直播|网络主播|YY_财经
- 999℃端午出行注意避开三座桥七条通道|出行大e点美胸组合|通道|路网
- 05-30为何皇子标配“乳娘”?她们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 05-30趣闻杂谈|清朝这个官职,名字很唬人却没有权力
- 05-30「史说黄瓜」三:鹿死谁手·残暴军阀?
- 05-30朱元璋到底埋在了哪里?让中国人头疼了600余年,至今成谜
- 05-29被大汉帝国击败的匈奴有多强大?余部仍能在欧洲兴风作浪
- 05-29第541章 当着她的面儿
- 05-29商周之战惊天动地,而一千年前,他们的祖先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 05-29顺治皇帝有8个儿子,为什么最终选择康熙继位呢?
- 05-29第601章 战前检验
- 05-29皇帝自黑真的有用?唐德宗自黑收获民心,而他自黑却亡国
- 标签列表
-
- 南通 (336)
- 历史 (249)
- 江苏 (108)
- 清朝 (86)
- 期货 (71)
- 明朝 (69)
- 不完美妈妈 (62)
- 铁路 (61)
- 南京 (61)
- 政治 (57)
- 高铁 (56)
- 经济 (55)
- 日本 (53)
- 江苏南通 (51)
- 上海 (45)
- 唐朝 (43)
- 文化 (43)
- 港口 (43)
- 房地产 (42)
- 新疆 (42)
- 楼市 (41)
- 宋朝 (40)
- 城市 (39)
- 朱元璋 (38)
- 康熙 (38)
- 开发区 (38)
- 银行理财 (38)
- 中国历史 (36)
- 刘备 (36)
- 曹操 (36)
- 三国 (34)
- 刘邦 (34)
- 房企 (34)
- 诸葛亮 (33)
- 长三角 (33)
- 成都 (33)
- 南通市 (33)
- 海门 (33)
- 汉朝 (32)
- 股权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