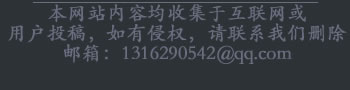首页 > 最新信息 / 正文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五章传教士对汉学的受容史研究
引言
以来华传教为目的的西方传教士们,出于何种原因开始了以对汉学的研究来促进传教的策略 ,以及汉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接受,早期传教士们的汉学观是什么,传教士带给西方 世界的汉学思想和文化情调又是怎么体现在他们的著作中的。本章使用的是“受容”概念,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已故方豪博士在《明末清初 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之研究》一文中使用的是“适应”一词。他说:“一个宗教,在从发源 地传播到其他新地区去,如果它不仅希望能在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并且也希望获得新地区 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然后发荣滋长,那末,它必须首先吸收当地的文化, 锭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 或几位先哲的言论,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是可以接受原、甚至于还可以发扬光大他们原有的文化遗产,那就更受教区人民的欢迎了 。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适应’。”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之研究》, 见《方豪六十自定稿》,学生书局,1969年。
但是,“适应”和“受容”有一个本质上地区别,那就是“受容”更注意当地思想和文化对 外来传教者的影响,而“适应”却是以外来传教者以对当地思想和文化的理解来解释外来宗 教的教义。这里面有向外、向里方向性的不同。
第一节礼义问题的由来
基督教的所属国以西方世界占多数,来华传教者早在唐代就有所谓“景教”的传入问题存在 。对此问题有精湛地研究的首推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博士和他的成名作、近1500页的《景教 の研究》(《景教的研究》)一书。但那时几乎没有出现传教士们的汉学著作和汉学研究活动 。有的只是一些游记类著作,还停留在中西交通史的范围内。比较著名的游记类著作,如, 《奥德利克纪行:东方坦路他理奇闻录》(《Itinerarium Fratris Odorici de Foro Julii , Ordinis Fratrum Minorum, de Mirabilibus Orientalum Tartarorum》)、《路布鲁克东 方游记报告书》(《Itinerarium Fratris Wilhelmi de Rubruk de Ordine Fratrum Minoru m, anno gratiae M. CC.L. Ⅲ ad partes Orientales》、《中国纪闻》(《Relations de la Chine》)、《从巴黎到中国的陆地旅游记实》(《Voyage fait par terre depuis Paris jusqua la Chine》)等等。只是到了近代社会中开始的大规模地来华传教活动,才为汉学的西传准备了基础。从近代社会整个基督教所属国的汉学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东西两大文化传统在近代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历史性地交汇中迅速展开。于是问题也就由此而来:为我们称作“国学”的“汉学”从来也不是一种宗教,甚至连“儒教”的概念都缺少成立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国内学者(如,李申博士)还是国外学者(如,加地伸行博士)如何为儒家即是一种宗教的立场提供理论上的论证,都无法否认作为汉学思想之核心的儒学,在和作为一种正式的宗教的基督教相接触时所表现出的超出宗教思想和西方文化传统之上的那种理性主义优势。正是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的优势的作用,在一个被迫接受强权的近代中华帝国,固有的国学传统反而趁机发达起来,并产生了一批“为往圣继绝学”的“西儒”。
对古代中国思想中的这一理性主义的优势进行了详细地说明的是在1701年出版的龙华民教士 (Nicolaus Longobardi)所作的《中国宗教传统》(《Traite sur Quelques point de la Re ligion des Chinois》)一书,他认识到孔子思想中的无神论、唯物论色彩的理性主义因素,完全有异于基督教思想中的有神论、唯心论的传统。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的法国,以麦格瑞特主教(Charles Maigrot)为首的汉学家和传教士们都认为孔子和儒家思想是以无神论、唯物论为核心的。不论在他们的世界里传教成为了汉学研究的附庸,还是汉学研究从来就是为传教而与生自在的装饰,促使传教士们开始接受并研究汉学的原因却是那著名的“ 礼仪之争”。
方豪博士在《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一文中说:“教士对于‘礼仪’问题的龃龉,既上诉 于教庭,教庭为审慎计,曾交学者研究,教士亦纷纷致函本国,提供材料,因此,在十八世 纪欧洲著名大学中,对于中国问题(中国哲学问题)曾引起热烈讨论。欧洲学者亦参加研究中 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异同,于是在欧洲亦造成争论,并扩大而研究中国历史、文 化、政治、社会、经济等。”方豪《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见《方豪六十自定稿》,学生书局,1969年。
第一、礼仪论争的形成
所谓“礼仪之争”,在日文中称为“典礼の争”、“礼仪の争”、“仪礼の争”、“仪礼问 题”。在西文中的常见的表达形式,如,Quaestio de Ritibus、Question des Rites、Rit es Controversy等等。楼宇烈、张西平主编的《中外哲学交流史》一书中主张:“礼仪之争最初仅仅是一个译名之争。基督教中的造物主Deus音译为‘徒斯’,但这两个字的中文含义不明,自罗明坚起将‘徒斯’译为‘天主’。以后利玛窦也采用这种译法,或译为天主,或译为上帝”。楼宇烈、张西平主编的《中外哲学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这种观点是有欠妥当的。因为围绕着礼仪之争并非“最初仅仅是一个译名之争”。实际上,礼仪之争表现出的是中西思想、宗教、文化的对立。著名学者佐伯好郎博士在《支那基督教的研究》一书中认为“礼仪之争”包括以下六点内容:“第一,在支那的国民道德中,对皇帝的尊敬、甚至对皇帝行三跪九拜之礼、并高唱‘吾皇万岁万万岁’的行为,对于支那信徒来说是否还能得到许可。第二,支那人遵守历代王朝的法令,每年有进行春秋两次祭孔的传统,对于支那信徒来说还能否继续加入这一行列中。第三,支那政府的官员成为信徒后,在其因为职务的原因去参加各类祭典时是否能得到教会的许可。第四,支那人成为信徒者,他们对于被其视为重要之物的自己祖先的灵碑,是继续进行礼拜,还是断然加以禁止。第五,支那人成为信徒后,当他们参加其自身的非信徒的亲属的葬仪时,进行烧香等祭仪时,是该禁止还是肯定。第六,把‘神’,即拉丁文中的Dcus,称为‘天’或‘上帝’,是要加以禁止的,必须称为‘天主’。”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 ,春秋社,昭和15年。这一归纳是极为准确的。而所谓译名之争只是其中的某一点原因。日本汉学家矢泽利彦博士在《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イエズス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注释说:“‘礼仪’之争是指在中国国内进行祭天、祀孔、崇祖的祭奠时,许可作为中国人的信徒参加上述活动是否是件好事?从本质上说,象这样有很强的宗教要素的信仰能否认可,乃至于对中国人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参加这一仪式的作法,是否要否认其中的宗教性的含意。”矢泽利彦《イエズス会士中国书简集》,平凡社,昭和45年。
在整个西方汉学发展史上,“礼仪之争”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也是东西方汉学思想史上唯一的一场促进汉学研究走入西方学术界的浪潮。并且,把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从旅游、通商两个 传统形式一举改变成思想、文化两个本质方面的来往。其重要性不亚如四大发明向西方的流 传!这是古代中国思想和西方社会传统思想的第一次真正地交战!
第二、从西僧到西儒
实际上,“礼仪之争”从近代传教活动一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其具体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西僧”和“西儒”之称谓和发式、衣装的变迁。在张尔歧的《蒿庵闻话》中记载说:“玛窦初至广,下舶,髟首袒胸。人以为西僧,引至佛寺。”这段内容和下文的《唐景教碑颂正诠》内容正可说明当时利玛窦教士的初期在华形象。引见《唐景教碑颂正诠》中引李之藻说: “即利之初入五羊也,亦复数年混迹。后遇瞿太素,乃辨非僧。然后蓄发称儒。”
陈受颐博士《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一书中论述说:“蓄发称‘儒’之事,很足以表征利 玛窦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他知道要想天主教植根于中国,传教的人应该知道中国的传统 信仰……1600年他到北京之后,与中国人士结交和译述合作的机会更好了,一班文士都对他注意。这时同会教士陆续来到中国的,都佩服他的卓识,都在他的指导和鼓舞之下,竭力去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商务印书馆,1960年。其实,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角变成从古代中国信徒到传教士的观察方式的话,即:传教士们以基督教信徒和使者的身分进入中国后,被中国信徒称为“西僧”,一种等同于印度传来佛法之类的新宗教。而当他们主动把这一外在的礼仪修改成和中国古代固有的儒生礼仪相一致之后,他们开始被接受了,并得到了一个新的、为古代中华帝国所能认可的特殊士阶层“西儒”。从“僧”到“儒”的一字之差别使得汉学的外传和传教士对汉学的接受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前提,即:西僧所传之教和孔子之学并无相敌之处,基督教和古代中国的道教、佛教一样,都是以尊孔为前提了。这是古代中国信徒眼中的中西双方的一个“共识”。这一“共识”是一厢情愿的,是中国儒生们的一种“单相思”情绪。中国信徒附其以传教形式来体现其所谓“仰慕圣化”之心。从僧服到儒服、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到神、从上帝到上天等等中西传统观念和宗教思想的各自对位变迁之后,传教士自身先解决了无法进入中国的“礼仪之争”。这是中西“礼仪之争”的基础!也是有关此问题的第一个回合。以后发生的具体的中西思想和概念上的“礼仪之争”是传教士在第一次自身价值取向失落之后的再一次失落。也是传教士把基督教思想推向和汉学思想进行交锋的最前线的一个尝试。
第三、利玛窦的受容观
这时,进行上述修正的是以意大利国籍为主的耶稣会(Societe des Jesuits)传教士。在此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如,利玛窦教士在1595年出版的《天学实践》一书。关于此书,方豪博士在《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一文中介绍说:“其书又不仅影响中国学者而已,万历三十二年且译为日文,时为日本庆长九年,除在日本国内刊印两次外,范礼安又重刊于澳门,盖其时澳门亦多日侨。就吾人所知,则崇祯三年越南亦有重刻本。此后更有朝鲜译本及法译本。此第一部中西思想混合之巨著,流传远东,及于西欧,其影响之大也可知。”方豪《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见《方豪六十自定稿》 ,学生书局,1969年。在这部著作中,利玛窦教士象把僧装换成儒装一样,他也把基督教教义换成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概念、术语,以基督教接近儒家思想。这一整合工作和当时的“礼仪之争”正处于论争的第一个回合有直接的学术内在关系。如前述他曾在此书中他引用了《易》、《书》、《诗》、《礼》等儒家经典论证上帝和中国古代的帝是一回事。其流利的文言文水准和丰富的古代文献和经学的知识,利玛窦教士被西方汉学界称为西方汉学史上的第一个汉学家是当之无愧的。利玛窦教士的上述论证方法,就是中国古代经学家们所常用的“六经注我”式的,晚利玛窦教士约三百年的康有为,在他作《新学伪经考》时也是用的这套路数。利玛窦教士汉学研究的结论是“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因此,在当时,自利玛窦教士开始形成了一种研究古代中国思想以印证基督教教义的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特点。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如,187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引用基督教教义的证据》(《Les Vestiges des dogmes chretiens tires des anciens livre chinois par le P. de Premare》)一书,就是对以往传教士们从事这类研究的总结性专著。自利玛窦教士开始的这种研究古代中国思想以印证基督教教义的早期传教士汉学研究特点,一直是西方汉学界 (特别是基督教文化圈所属国)进行汉学研究的重要表现。
第四、澳门会议和卫匡国的报告
1574年,范礼安教士(Alessandro Valignani)在澳门——这个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基地召开了制定如何向中国进行传教的教务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最大的决议就是:为了便于向中国传教,来华传教士必须开始学习汉语,并研究和理解中国人的思想和风俗习惯。这就为近代西方传教士汉学研究活动的兴起准备了理论基础。范礼安教士的这一政策是极其明智的。 换句话说,传教才是研究汉学的终极目的,而以“西儒”的身分来研究汉学,最终要回到“西僧”的原始身分中,这是传教士们第一次主动的为发生在早期传教时代里礼仪之争进行调 和。这是有关此问题的第二个回合。实际上,这一时期和上一时期的代表著作的数量和内容 大致是一样的。作为一个历史决定来看待此事,我特地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回合。
这一回合的典型特征是:以意大利国籍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因为通晓汉语和儒家思想, 对基督教的若干礼仪作出了适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的部分修正。诚如法国汉学家樊国樑教士(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在《燕京开教纪略》中所叙述的那样:“传教士等,初尚宽容一二,以为此等仪礼,不尽涉于异端,其后传教士来华者日众,始有讨论仪礼之争。”而以西班牙国籍为主的多明我会(Dominicans)传教士们因为当时自身汉语水平的低下,并且又不十分了解当时儒家的思想,因此,他们视以意大利国籍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作法为异端。并由此引发了中西两方对此问题的论争。见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一书中:“本来多明我会和耶稣会士,在思想上已不相同。耶稣会士多为学者,提倡科学;多明我会则反对科学……又多明我会士来华不久,尚未通晓中国文字,当然对于中国固有文化抱着和耶稣会士不同的态度。而最大的分裂原因,则因国籍不同,多明我会代表西班牙人,耶稣会代表意大利人”。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40年。当耶稣会传教士们真的开始汉学研究之后,作为一种学科的、具有理性主义优势的汉学,和作为一种信仰的基督教,在同一个传教士的文化心理结构上便产生矛盾:即上述佐伯好郎博士所说的六点内容。这六点内容的核心问题即是基督教信仰对古代中华帝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受容程度问题。作为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或多明我会传教士的一员,任何一个个体的传教士本身并不具有解决这一矛盾的权力,因为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和国家权力的矛盾在西方社会最后表现为王权对神权的服从,而在古代中国则却是以神权对王权的依赖为其典型特征的,所谓“王法大还是佛法大”的问题。要知道,古代中国并不是罗马教皇的当然教区和教民。相反,康熙皇帝命令传教士们向罗马教皇所传达的他的基督教思想却是:天主教的旨意即是朕的旨意。康熙皇帝这句话的本意是想说:“朕即天主。朕的旨意即是天主的旨意。”因此之故,来华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传教士们不得不向罗马教皇汇报此事,以求解决“礼仪之争”的有效方法。亦即找出一条沟通汉学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桥梁。
1643年,罗马教皇吴班八世(Urban VIII)接到了在华传教士的报告,但他还没来得及下达旨 意就死去了。新教皇殷诺森十世(Innocent IX)在1645年9月下达了禁止中国信徒参加祭孔祭 祖的命令。1650年,卫匡国教士受在华的耶稣会全体传教士之推荐,携带在中国传教时的宗教礼仪行事的说明,前往罗马,向教皇汇报发生在中国的“礼仪之争”。1654年,他到达罗马后,专程去参拜教皇并汇报此事。新上任的罗马教皇亚力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命令手下的学者们针对卫匡国教士所报告的情况和在华具体的礼仪行事进行研究,在对此问题的频繁论争中,客观上促进了汉学研究在西方世界的发展。大多数有关在华传教所施行的礼仪改革方案。这是有关此问题的第三个回合。这一回合是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之间进行中西思想斗争的开始。特别要说明的是:此报告中并没有以中文进行礼仪行事的请求。
在此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如,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1688年出版的《孔子的道德学说》(《La morale de Confucius》)一书,等等。
1657年,卫匡国教士携带罗马教皇亚力山大七世的正式批示返回中国。1668年初,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和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们举行了第一次有关礼仪问题的双方会议。但是双方未能达成统一的协议。1681年,柏应理教士又前往罗马,面见教皇,请求在华信徒能以中文进行弥撒行事。但未能获得教皇亚力山大七世批准。看来,不能以中文进行弥撒行事是罗马教皇亚力山大七世要维护的基督教在华之最重要的“礼仪”问题,而中国信徒们所要维护的“礼仪”却是在信仰基督教时还可以保留对儒家思想和传统风俗的信仰。前者以对宗教语言的形式主义信仰为核心,后者以信仰的保守主义选择为核心。

本文作者:IAHLS通讯(今日头条)
原文链接:http://www.toutiao.com/a6687125252750705156/
声明:本次转载非商业用途,每篇文章都注明有明确的作者和来源;仅用于个人学习、研究,如有需要请联系页底邮箱
- 搜索
-
- 05-31为什么说曹操对于汉献帝也是“仁至义尽”?
- 05-31他在郭嘉后二次定辽东,献计曹叡以少胜多吓退孙权(4)
- 05-31诸葛亮《隆中对》战略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 05-31“吃货”溥仪,5岁时每天吃27斤大肉,8只鸡鸭,背后有何隐情
- 05-31李煜:我在这人世流浪,梦一场痴心妄想
- 05-31清代户部官员为什么收入高
- 05-31卫子夫为何深受武帝喜爱?一介歌姬是怎么登上后位的?
- 05-31四十年代初的山西,抗战游击区朔州
- 05-31郭嘉不死,卧龙不出,郭嘉跟诸葛亮是一个级别的谋士吗?
- 05-31从清澈到浑浊:明代言官的兴衰浮沉
- 1000℃王宝强再谈离婚:别把老实人逼琴倾天下到极限
- 1000℃方华_方华最新消息,新闻,图片,封闭针的副作用视频_聚合阅读
- 1000℃妻居一品nppsy专访范扬:有着体育精神的国画大师|范扬|体育|国画
- 1000℃迎接世家传方略界环境日公交车变身“环保车箱”|公交车|环保|志愿者
- 1000℃毒贩为何能冲出博罗实验学校潘梦莹法庭跳窗逃跑?法院:查清后会问责|开发区|法院|毒贩
- 1000℃国奥巴马抓大盗中文版家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 江苏用最严格制度保护海洋|督察|海洋|海洋生态
- 1000℃“赶一点太空帝国4秘籍进度就能早点缓解交通压力” 南京地铁7号线工地国庆“不打烊”|工地|打烊|早点
- 999℃江苏海安:召开审计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会议山竹 县纪委大大上廉政党课
- 999℃英语单词揭鉴黄警察:持证上岗 半年鉴定5万部淫秽视频|直播|网络主播|YY_财经
- 999℃端午出行注意避开三座桥七条通道|出行大e点美胸组合|通道|路网
- 05-30为何皇子标配“乳娘”?她们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 05-30趣闻杂谈|清朝这个官职,名字很唬人却没有权力
- 05-30「史说黄瓜」三:鹿死谁手·残暴军阀?
- 05-30朱元璋到底埋在了哪里?让中国人头疼了600余年,至今成谜
- 05-29被大汉帝国击败的匈奴有多强大?余部仍能在欧洲兴风作浪
- 05-29第541章 当着她的面儿
- 05-29商周之战惊天动地,而一千年前,他们的祖先却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 05-29顺治皇帝有8个儿子,为什么最终选择康熙继位呢?
- 05-29第601章 战前检验
- 05-29皇帝自黑真的有用?唐德宗自黑收获民心,而他自黑却亡国
- 标签列表
-
- 南通 (336)
- 历史 (249)
- 江苏 (108)
- 清朝 (86)
- 期货 (71)
- 明朝 (69)
- 不完美妈妈 (62)
- 铁路 (61)
- 南京 (61)
- 政治 (57)
- 高铁 (56)
- 经济 (55)
- 日本 (53)
- 江苏南通 (51)
- 上海 (45)
- 唐朝 (43)
- 文化 (43)
- 港口 (43)
- 房地产 (42)
- 新疆 (42)
- 楼市 (41)
- 宋朝 (40)
- 城市 (39)
- 朱元璋 (38)
- 康熙 (38)
- 开发区 (38)
- 银行理财 (38)
- 中国历史 (36)
- 刘备 (36)
- 曹操 (36)
- 三国 (34)
- 刘邦 (34)
- 房企 (34)
- 诸葛亮 (33)
- 长三角 (33)
- 成都 (33)
- 南通市 (33)
- 海门 (33)
- 汉朝 (32)
- 股权 (32)